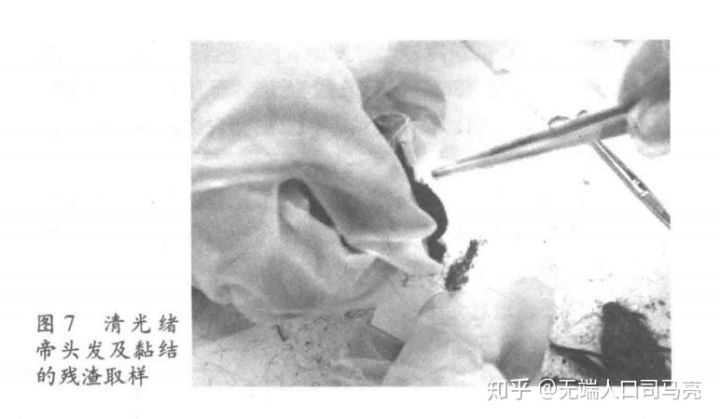本文发表于《新京报》2022年4月22日。
David Strand. Rickshaw Beijing: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.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9. 364 pages. ISBN: 0520082869
史谦德:《北京的人力车夫: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21年。ISBN: 9787214224866.
1980年代中期开始,以罗威廉(William Rowe)《汉口》两部曲的发表为标志,美国汉学界一度出现过一种研究倾向,关注中国近代政治、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领域、精英自治运动乃至“市民社会”的出现过程。在这一研究趋势中,最常被提到的著作有五部,分别是:
- 罗威廉:《汉口: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(1796-1889)》(中译本于200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);
- 罗威廉:《汉口: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(1796-1895)》(中译本于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);
- 冉玫烁(Mary Rankin):《精英行动主义与中国政治转型:浙江省,1865-1911》(斯坦福大学出版社,1986年);
- 萧邦奇(Keith Schoppa):《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:20世纪初的浙江》(中译本于202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);
- 史谦德(David Strand):《北京的人力车夫: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》(中译本于202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)。
在这一史学潮流中,除最为引人注意的罗威廉外,接踵关注城市政治及其产生背景的研究,即为史谦德《北京的人力车夫: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》一书。该书脱胎于作者198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《1920年代的北京:政治秩序与大众抗议》(Peking in the 1920s: Political Order and Popular Protest),1989年正式以著作的形式出版精装单行本,1993年又出版平装本。现今该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,成功弥补了关于中国城市政治史汉译上一枚“遗珠”的缺憾。
继续阅读“书评:史谦德《北京的人力车夫》”